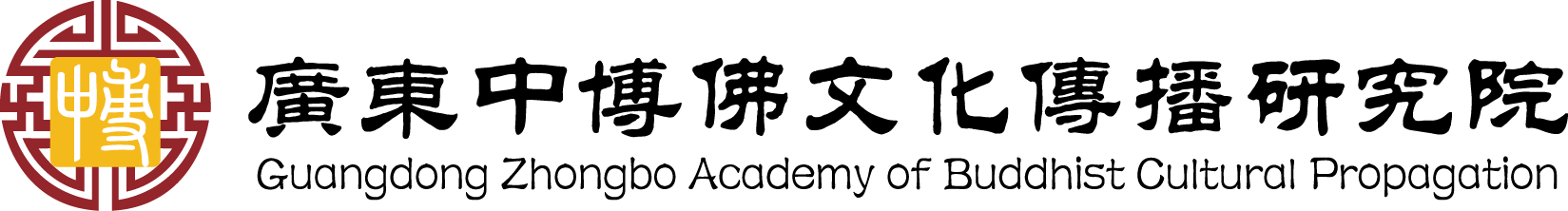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法师
引言
中国佛教史上有一部经典,它非佛所说,却被冠以“经”之圣名;它不仅开创了汉传佛教八大宗派之一——禅宗的新格局,而且为中国文化缔造了一种全新的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禅的精神。从此,儒家“止于至善”、修齐治平的道德理想与人生责任感,道家“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无为而无不为” 的自然、自由精神,和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离世间觉”的当下觉悟精神,不断交融激荡,共同铸造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传统——以人为本,以心为归。
一种外来宗教或文化要想成功地实现本土化,并产生长远的生命力,首先要适应本土文化的传统、符合本土人群的现实需要,同时要具备启发、推动本土文化不断自我更新、丰富发展以及引领人们趋向精神超越和心灵觉悟的创造潜能。两千年来,佛教的中国化正是佛教面对不同时代的中国文化和现实中的中国人,不断适应与创新的过程。深入观察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轨迹与内在脉络,会发现中国佛教的传播、发展、演变、流布不仅是佛教自身生存发展、弘扬光大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文化更新嬗变、自我扬弃的需要,是中国人突破精神困境、寻求心灵解脱、实现自我完善的需要。佛教中国化历程中所有的重要理论与重大实践成果,都是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发展需要的圆融与契应,因此,佛教的中国化从来都不是一种被动的同化,而是主动的创造。
中国文化的特征,有局部的、暂时的,也有根本的、一贯的;中国人的现实需要,同样有眼前的、表层的和永恒的、内在的。禅宗正是抓住和适应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及中国人生命的内在深层需要,所以能在一千多年的岁月时空中深入人心、历久弥新。作为禅宗开宗立派的根本经典,《六祖坛经》正是通过惠能大师的生命证悟,通过他对大乘心法的创造性理解,使佛教真正融化为中国文化的血液,让佛教真正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和生命;千载之下,《坛经》与禅宗精神依然可以和现代中国人的生命发生呼应,可以进入平凡的生活,成为我们现实的一部分。因此,在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中,惠能大师和《六祖坛经》树立起一座精神的丰碑,不仅是中国佛教完全本土化的标志,而且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影响至深至远,犹如智慧之源泉,源远流长;亦如心灵之明灯,烛照四方。
一、从“积”到“消”——惠能大师对佛教中国化成果的创造性继承
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规律,钱穆先生提出“积消循环”之说。他认为,“学术思想有两大趋向互相循环,一曰积,一曰消。……学术思想之前进,往往由积存到消化,再由消化到积存。正犹人之饮食,一积一消,始能营养身躯。同样,思想积久,要经过消化工作,才能使之融汇贯通。观察思想史的过程,便是一积一消之循环。”在他看来,对中国学术思想史影响甚巨的“两大伟人”,其一便是六祖惠能大师,其二则为理学家朱熹,此二人正是“能消能化”与“能积能存”的典型。
在惠能大师出现以前,佛法由印度传入中国已历经数百年,从无到有的佛教不断探寻着与中国本土文化契合交融的途径,通过丰富的经典翻译、精妙的义理诠释、深入的禅法观修,持续沉淀着厚积薄发的创造潜能。
大乘经典铸就了中国佛教思想大厦的宏博根基。比如大小品《般若经》《维摩诘经》《金刚经》《法华经》《涅槃经》《华严经》《楞伽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大智度论》《中论》《大乘起信论》等。从这些代表性经典的翻译、诠释中不仅派生出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众多学派,而且为隋唐宗派佛教的创建提供了基本经典依据和丰富思想源泉。
学派与宗派的脱颖而出,是佛教真正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的标志。两晋南北朝时期,般若、毗昙、涅槃、成实、俱舍、三论、地论、摄论各家如百花齐放。在义学思潮中诞生了如道安、慧远、僧肇、道生等中国本土的佛学大师,无论是“格义”之法,还是佛法与玄学的融通,都推动佛教与当时的主流文化思潮契应结合。《肇论》四篇——《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涅槃无名论》,其主题都是借用或化用了玄学名词,并以玄学思维能够理解的方式演绎般若空性,成为佛教中国化的早期理论经典。道生法师敢于提出迥异流俗的一阐提人“皆得成佛”及顿悟之说,更是佛教义理由“积”而渐趋于“消”的体现。正是基于持续不断的思想积累与创造转化,才有了隋唐时代宗派佛教的兴盛。
唐代八宗皆是在中国本土创立的独立而完整的教证体系,尤以天台、华严、禅宗最具中国特质。在惠能大师出现的时代,天台、华严已经建立起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天台宗摄取《般若经》《大智度论》《中论》等空性中观思想,华严宗融摄了《密严经》《楞伽经》《般若心经》《大乘起信论》《法界无差别论》《十二门论》及地论、摄论等经论、学说,都可谓集大乘佛法之大成。而最关键的是,他们并不是对印度佛教学统的单纯继承,而是以这些大乘经典为依据,展开基于实证经验之上的独立创见(如智者大师悟入法华三昧,杜顺和尚证得华严三昧)。天台之“性具实相”“一心三观”“一念三千”“五时八教”,贤首之“六相圆融”“十玄无碍”“法界缘起”,都是中国祖师创造性思维和圆融智慧的体现,因此二宗“也可以说是大乘佛教思想史上的两个特异的奇峰”。
从安世高翻译《安般守意经》之后,禅法即传入中国。在惠能大师以前,已经有安般禅、五门禅等小乘禅法,以及以净土宗为代表的念佛禅和以台贤二宗为代表的实相禅。但按太虚大师来看,这些禅法还都属于“依教修心禅”的阶段,也就是依照戒定慧次第修行,属于印度“如来禅”的范畴。而真正的中国“祖师禅”,却是到惠能大师时期才创立的。
在《六祖坛经》中,可以明显看到各种大乘经典的法脉流动,也能看到惠能大师对净土、天台等其他宗派的高度圆融姿态,甚至可以看到对传统儒道精神的吸取融合。比如《金刚经》等般若经典之无相、无念、无住,《维摩诘经》之“不二法门”,《涅槃经》之佛性思想,《楞伽经》之“如来藏”思想,《大乘起信论》之“一心开二门”等;在应机教化弟子时,他提出“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心悟转法华”等说法,却没有否定对净土和《法华》的修持。这些都说明,惠能大师开创的南宗禅法虽有“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特点,但其本身却是对汉魏晋南北朝至初唐佛教的总集与提纯,并能以“心法”贯通各大宗派。因此,《六祖坛经》所体现的禅宗思想,不是宗门与教下的对立,更不是对前代佛教源流的否定,其对佛教中国化的革命性贡献,恰恰是对历代以来中国佛教传统的兼收并蓄和创造性转化,使佛教真正消化、融化、内化于中国的思想文化体系,并对当时和未来人们的修行证悟、现实人生产生持久的指导意义。
二、从“渐”到“顿”——《六祖坛经》对佛教中国化的革命性贡献
经过汉魏至隋唐几百年的流传演变,佛教的中国化发展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经典积累、深入的思想梳理、独立的理论创建和丰富的大乘禅法实践,产生了各具特色的本土宗派。但是面对深广的理论体系、精微的名相义理、高超的禅观境界,一般人依然难以把握和真正契入。怎样把佛法与人的这种“隔膜感”彻底打破,让大乘佛法能够内在化、现实化、生活化、普及化,真正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融入中国人的生活和生命?这便是佛教中国化核心层面的命题。惠能大师和《六祖坛经》的出现,正是对这一命题的破解。
1、顿悟成佛说对中国佛教的根本超越
惠能大师对中国佛教的贡献不是一般的继承与创新,而是几百年来大积存之后的大消化。所谓的“大消化”就是从全面汲取中酝酿出了真正的精髓,如《大般涅槃经?圣行品》所说:“譬如从牛出乳,从乳出酪,从酪出生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出醍醐。”这个“醍醐”就是“顿悟成佛”之说。此说对于佛教中国化的革命性贡献在于,从此将“渐修”“渐悟”的佛教带入了一个当下觉悟、当下解脱的新时代。
(一)“当下性”的二重指向
太虚大师在《佛学之源流及其新运动》中这样评价六祖所开创的中国顿悟之禅:“最雄奇的是从中国第一流人士自尊独创的民族特性,以达摩西来的启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而直证释迦未开口说法前的觉源心海,打开了自心彻天彻地的大光明藏,佛心自心印合无间。与佛一般无二的圆明了体现了法界诸法实相,即身便成了与佛陀一般无二的真觉者。然后应用一切方土的俗言雅语,乃至全宇宙的事事物物,活泼泼地以表现指示其悟境于世人,使世人各个直证佛陀的心境。此为佛学之核心,亦为中国佛学之骨髓。惟中国佛学握得此佛学之核心,故释迦以来真正之佛学,现今惟在于中国。”
这段话指示出顿悟成佛说的两个关键层面:一、直探心源觉海,顿证诸法实相,即身成就佛道;二、融通心法世法,万物皆为悟境,即现实而成佛道。这两个层面共同构成了顿悟成佛之“顿”,即为觉悟和解脱的“当下性”。这个当下,一方面指向内心,即心性的当下觉悟;一方面指向现实,即人在现实中觉悟。顿悟成佛意味着,解脱和超越就在当下,就在每个人的心里,就在人的每一种行为里。也就是说,宗教修行的终极目标、终极追求和人的当下实存是同时的、同体的,没有时间、空间的距离和障碍——这无疑是一种精神领域的重大发现和革命。
《坛经》一开始便开宗明义:“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直呈顿悟成佛的宗旨。又云:“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是以将此教法流行,令学道者顿悟菩提。各自观心,自见本性。”又云:“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自不有,故知万法本自人兴。”并有“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之名言。这些都表明,“真如本性”可以被“顿见”,因为它本来就在每个人心里——“万法尽在自心”;而这种“顿悟”“顿见”并不是脱离世间的抽象存在,它恰恰隐含于人们的一言一行中,在现实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有觉悟成佛的无限可能性。
(二)根本超越的实质内涵
在惠能大师之前的时代,中国已不乏顿悟成佛说的先驱,比如晋宋之际的道生法师,认为只有在菩萨十住位时的彻底觉悟,才算是真正的顿悟成佛。因为“夫称顿者,明理不可分,悟语照极。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理智恚释,谓之顿悟。”这里的“不二之悟”即非分分证悟,而是一次性地彻底觉悟。道生法师虽认为“一阐提人”亦有佛性,皆得成佛,但他的顿悟说却划定了“十住位”的界限,实际上还是消解了凡夫当下顿悟的可能性。而到了惠能大师,则将凡夫顿悟成佛的渺小可能性提升为当下成佛的必然性,如云:“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更云:“后代迷人,若识众生,即是佛性。若不识众生,万劫觅佛难逢。”
也可以说,惠能大师以前的佛学大师们都在尽各自的努力,发掘和证成着凡夫成佛的可能性,从般若空性到涅槃佛性再到如来藏性,全都围绕着凡夫如何逼近真如实相的问题。即便是强调“以心印心”的达摩禅法,在实际传承中也依然没有彻底舍弃“渐修”“渐悟”的传统。比如“二入四行”之“理入”者,“谓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想所覆,不能显了。若也舍妄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于文教,此即与理冥符,无有分别,寂然无为,名之理入。”还是要“藉教悟宗”“凝住壁观”。及至五祖弘忍的东山法门,仍然强调通过坐禅渐修、渐悟,如云:“尔坐时平面端身正坐,宽放身心,尽空际远看一字,自有次第。若初心人攀缘多,且向心中看一字。证后坐时,状若旷野泽中,迥处独一高山,山上露地坐,四顾远看,无有边畔,坐时满世界,宽放身心,住佛境界。清净法身,无有边畔,其状亦如是。”
只有到了惠能大师,才真正打破了对禅法形式的拘泥,超越了渐修渐悟的传统,将成佛的可能性变成了一种必然性。《六祖坛经》中对禅定是如此描述的:“善知识!何名坐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善知识!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又曰:“学道常于自性观,即与诸佛同一类。吾祖惟传此顿法,普愿见性同一体。”能够自见本性清净,便可觉悟成佛,六祖所创造的其实不是禅法,而是心法。所以,惠能大师顿悟成佛之说对中国佛教的根本超越和创新,本质上也并非方法问题,而是见地问题。正因为见地的不同,最终带来了方法和形式上的革命性变化。
其实,在禅宗最初的渊源——“拈花微笑”公案里,就没有借助任何修行方法。它本身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觉悟,觉悟就是成佛。所以,真正的顿悟精神,并不是禅修,也不是参话头,而是心灵觉悟的当下性、无碍性、直接性、必然性,这也可以说是中国禅宗的真精神。这种“禅”之精神可以体现在现实生活的任何场景中,可以流淌于任何人的生命活动中,它对于现实人生来说不再是一种“异己”的存在,而是“不二”的、一体的,佛法的亲切感从此深深植入了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和文化血脉。
2、顿悟成佛说与中国文化的根本圆契
惠能大师的顿悟成佛之说让佛法回归到了人本身、心灵本身,同时也回归到了现实,回归到当下。这种对人心、人性的自觉、自信,对现实人生的终极关怀,形成了大乘佛法与中国文化根本、内在的交汇点。由此,心性的觉悟与现实的关照融为一体,超越精神与现实生活获得了统一,禅宗实现了与中国文化的深度契合,与中国人生命的内在融合,乃至成为唐宋以后“民族思想全部的根本精神”。
(一)圆融契合点之一:自我心性的觉悟
中国文化本身即为重视心灵的文化,内省、内求、自觉、自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的特殊品性。
在儒家经典中,内省、内求不仅是自我道德修养的方法,同时也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因此可说是中国文化根本、一贯的精神。比如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曾子每日“三省吾身”;孟子则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又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在道家思想中,对“道”的体会同样来自对内心的观察体悟。如老子主张“致虚极,守静笃”;庄子提出“心斋”“坐忘”之说。
内省、内求源自对真心本性的自觉和自信,也就是对心性的体认。如《大学》一开篇即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对人人皆有的“明德”的体认,便是一切内省内修功夫的前提;孟子主张“尽心知性”“存心养性”;老子则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这种内省、内求、自觉、自信的传统文化特质在《坛经》中处处可见。比如,六祖始见五祖,就开门见山提出:“惟求作佛,不求余物。”当五祖嘲笑他:“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六祖即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体现出对自我生命觉悟充分的自信。带着这种自信,六祖于五祖言下大悟,彻见了自性本心的伟大:“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正因为惠能大师本人即是从不识一字的“獦獠”而大彻大悟的,所以他由自信、自觉、自证、自悟而生起对一切凡夫众生必能顿悟成佛的无上信心,并力图引导众生深深忍可、悟入这一真相。如云:“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菩萨戒经》云:‘我本元自性清净。’善知识!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正是围绕着人的主体性、自觉性、无限性、创造性,惠能大师以大乘心法圆融了中国传统文化,契合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并使明心见性的思想成为后来中国文化创新发展的智慧源泉。
(二)圆融契合点之二:现实人生的关照
中国文化的终极追求向来都植根于踏实的道德实践,中国文化的现实性并非世俗性,而是一种清醒和责任,是一种生命的融入感和悲天悯人的情怀。所谓对“现实人生的关照”,意即个人与群体、当下与历史、此地与他方之间存在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因此,人的觉悟也应于社会群体生活中、于历史文化演进中、于时空因缘变化中具体展开。觉悟与生活,解脱和现实,是一体不二的。
譬如《中庸》里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又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这些话都表明,“道”与现实人生是融为一体的,即使在愚夫愚妇身上,“道”的本性也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中国人的信仰追求一定是落实于最平凡的日用生活之中,天人合德,素位而行。
《六祖坛经》中的惠能大师,从出身、求法、避难、弘法、传法到圆寂,其生平本身就是最好的修行觉悟实践,其人生也可视作佛教中国化最真实生动的写照。大师生于岭南边地,家贫卖柴、不知文字,却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后求法五祖,八个月在磨坊腰石舂米,直至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之后的六祖没有住在寺庙里天天坐禅,而是逃到猎人队里生活了十几年,食“肉边菜”。最后终于剃度出家,大弘顿悟心法,从此禅宗法脉不断、源远流长。六祖的生活和修行是全然一体的,这种修行方式不仅是印度佛教所未有,与之前中国的祖师大德们也大相径庭。这种平民化的觉悟历程为后来的禅宗开辟出了极为活泼生动的禅机妙用,搬柴运水、生活日用、乃至一花一竹都是禅,举手投足、一问一答、或棒或喝也都是禅——觉悟的因缘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当下。诗人王维为惠能大师所作碑铭中这样描述其思想行谊:“根尘不灭,非色灭空;行愿无成,即凡成圣。举足下足,长在道场;是心是情,同归性海。”正是六祖觉悟心性、不离世间的真实写照。
三、从“源”到“流”——《六祖坛经》对当代佛教中国化的启示
惠能大师和《六祖坛经》开辟出了一个佛教文化的新天地,此后“一花开五叶”“马祖开丛林,百丈立清规”,禅宗从法脉传承、思想理论、修行方法、组织制度、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全面实现了佛教中国化。同时,催生了宋明理学、王阳明心学、道家内丹学,并对中国的文学艺术、人生理念和生活方式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惠能大师的思想成果改造了中国的民族性,为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和自我更新贡献了永不枯竭的生命力、创造力及灵感源泉。在今天,当代佛教正在开辟中国化的新时代和新境界,从《六祖坛经》的丰富内涵中,我们可以获得新的感悟和启示。
1、回归心源,觉悟人间
佛教中国化不是一个历史的命题,而是一个时代的命题。所谓佛教的中国化,其实本质上是中国佛教在每一个时代的“当代化”问题。
惠能大师在一千三百多年前所面对和解决的,正是唐代佛教在集大成基础上实现彻底本土化和根本性超越的时代课题。而这一课题的核心,其一是文化问题,其二是人心问题。也就是文化的范型和人心的需要决定了中国佛教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应变。从《六祖坛经》的时代到今天,中国社会和文化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佛教的中国化同样要清醒地观察和面对当代中国的文化现状,以及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现状。
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文化不断渗入中国社会,在这一百多年中,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断遭到质疑和消解,而全球化风潮的席卷,更使中国社会陷入了多元文化和多重价值观的发展“陷阱”。失去传统文化根底支撑的价值多元化,在带给现代中国人开放视野的同时,也将人心带入了新的迷茫,个人中心主义、物欲主义、理性主义等西方文明弊病更加重了这种精神困境。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佛教,所要面对的最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重建中国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的问题。这个核心价值观是一种综合概念,它不仅应联结历史、传承传统文化命脉,而且要沟通世界、融合西方文化精华,还要应对现在、契应人们的现实需要,同时通向未来、指引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新方向。
这意味着,当代中国文化和中国佛教一方面要应对如何吸收转化西方文化的问题,同时要面对如何继承复兴传统文化的问题;或者说,是如何将东西方文化进行新一轮“大积存”后的“大消化”,将二者的精华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文化新的生命。因此,当代佛教中国化的时代命题,就不仅仅是中国佛教自身发展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如何面对西方文化及自身传统的问题。
惠能大师曾经成功地融合了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其顿悟说正是抓住了两种文化的根本契合点,给予人们当下觉悟、即世解脱的真正可能性。六祖开悟时说“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不啻为破解现代文明病桎梏的心灵密码:心灵是万法之源,人的价值是通过心灵觉悟来彰显和体现的;无论个人生命的解脱,还是对宇宙真相的接近,都可以回归到当下一念的觉悟。这种“心文化”特质不仅是禅宗的特色,也是大乘佛法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复兴弘扬“心文化”,对于联结传统与现代的断裂,消弭物质与心灵的对抗,重建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启示人类文明的新方向,具有根本意义。
当代佛教的中国化,一方面要回归文化源头、回归心灵源头;另一方面要发扬“不离世间觉”的精神,不离世间,觉悟人间。善巧运用现代科技文明传播佛法智慧,将“心文化”理念以现代化、形象化、生活化的方式亲切植入人心,并与世界文化交流互鉴,这些都是当代佛教需要积极开拓创新的领域。以“心文化”为价值导向,中国当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建才能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物质与心灵之间找到最大的文化公约数,为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健康持续发展带来生生不息的力量——而这,正是中国佛教现在和未来的致力方向。
2、回归经典,引领时代
佛法的住世弘扬、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都需要三样东西:一经典,二师承,三制度。六祖之后,禅宗的发展偏重“以心印心”“不立文字”之“教外别传”,却逐渐忽视了经教研学和戒律持守,致使禅宗的创造力日益衰退,或者与其他宗派合流,或者徒具形式,顿悟成佛的真精神和丰富内涵逐渐模糊、丧失。如太虚大师感慨:“中国古时虽能会教明禅,然未能从教律之次第上,而稳建禅宗,致末流颓败,一代不如一代也。”
反观《六祖坛经》,其中不仅能品尝到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主要大乘经典的法乳甘露,而且惠能大师本人亦说:“执空之人有谤经,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语言。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见人所说,便即谤他言著文字。汝等须知,自迷犹可,又谤佛经。不要谤经,罪障无数。若著相于外,而作法求真;或广立道场,说有无之过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得见性。但听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于道性窒碍。若听说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无住相法施。”六祖反对的不是文字本身,也不是“依法修行”,而是对“文字相”的执著。他又说:“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观照故,不假文字。”这里的“不假文字”“心开悟解”,前提还是闻法——“闻说《金刚经》”。所以“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并不是将佛法(觉悟)和文字对立起来,而是说明真正的觉悟是对包括文字在内的一切诸相的超越。
同理,惠能大师提出“无相戒”之说,也是引导人们通过内心的净化和觉悟来真实持戒,而非抛弃戒律。与此相关,关于修行觉悟的“顿渐”问题,六祖如是说:“法即一种,见有迟疾。何名顿渐?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在高唱人人皆可顿悟成佛的同时,也不否认不同根机众生有觉悟的先后快慢之别。
《六祖坛经》的丰富意涵启示我们:当代佛教中国化需要正确处理好教与证、理与法(戒律、制度)、修与悟、次第与圆融等相互关系,并将其汇归统摄于大乘心法之中。因此,我们不仅要继承古代宗派佛教的优秀成果,更要探索建立完整的汉传佛教修学体系。其中,首要的基础是对以大藏经为代表的汉传佛教经典的全面整理研究。汉文大藏经的校勘、整理、研究、翻译,不仅是建立汉传佛教完整修学体系的根基,而且是创新当代佛教思想理论、复兴传播中华文化乃至融合东西方文化的重要起点。因此回归经典、深入经藏是一项最基础而又最高端的工作。
当代佛教的思想建设格局实际超越了历代,其面对的不仅仅是汉传宗派佛教,还包括三大语系在内的整个中国佛教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多元文化。因此三大语系的佛教典籍、儒道等传统文化经典以及世界文化经典,都需要兼通并融。只有在充分积累、吸纳、研究和借鉴基础之上,才能创获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佛教思想理论,不仅为中国更为全世界提供足以引领时代的人类文明新理念。
结语
重新解读《六祖坛经》,犹如重温了佛教中国化的丰富历程。纵观两千年来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与中国人生命的共鸣,会感到民族文化传统和精神根底的重要性。六祖提出顿悟成佛说,之所以在当时社会引起持续反响和深广发展,主要是唐宋时代传统文化的精神命脉一直在延续,而且充满活力。今天佛教的中国化要开创出新的境界,所要面对的不仅是现代中国,更要面对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因此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推动“心文化”的复兴和创新发展,是我们需要担负的时代使命。只有让东西方文化在“心文化”中相遇相融,才能使佛教发展拥有无限广阔的未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