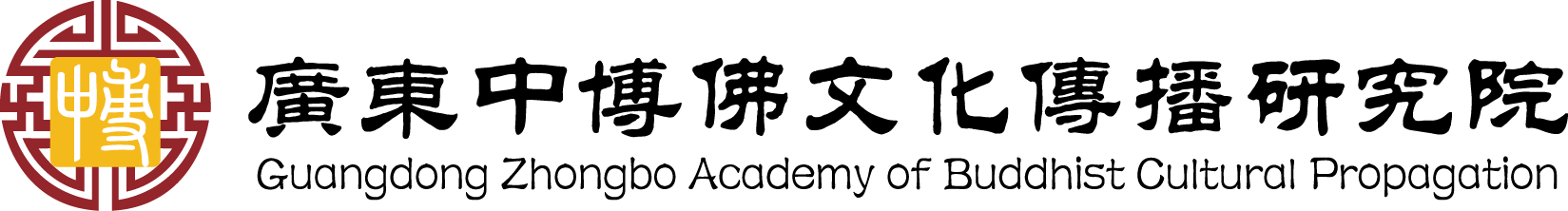有史以来,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曾对人类的文明进程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但是,这些历史事件在当时不一定是轰轰烈烈、光彩夺目,它们的壮丽辉煌,要过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才能为世人所瞩目、所理解。对于占人类总数大约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来说,佛教的初传,正是这样一次历尽千载愈显可贵的历史机遇。当年的中国人抓住了这个机遇,何尝会想到,正是这个机遇,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传统注入了一股永不枯竭的甘泉;正是这个机遇,使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传统驶向了一片蔚蓝的无边无际的智慧之海。
是谁抓住了这个机遇?是谁为我们送来了佛法?其功不可没,其名不可泯。特别不应忘记的,是它记下了中国佛教的起点。数典岂可忘祖?我们要为中国佛教的千年诞辰做一次隆重的纪念。
目前,有关佛教初传中国的纪年,主要有两种论点:一、伊存授经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即西元前2年),二、永平求法说(汉明帝永平十年,即西元67年),相差69年,大约三代人的时间。
永平求法说,在中国历史上长期流传。其实,此说法当初并非佛教界自身所认定。据汤用彤、任继愈、杜继文等学者考证,“汉明感梦”的说法,首见于后赵著作郎王度上石虎(西元334年)之奏议:“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高僧传·佛图澄传》)
其后,在诸多攻击佛教的文献中,此说法屡屡被采纳。例如,北魏太武帝在太平真君七年(西元446年)取缔佛教的诏令中说:“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唐韩愈在《论佛骨表》中则说:“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汤用彤先生认为:“而《谏迎佛骨》一文,既为后人所传诵,故此说更认为定论。”
佛教方面接受了“永平求法”的说法,亦有自身的无奈。汤用彤先生认为:“汉明为一代明君,当时远人伏化,国内清宁,若谓大法滥觞于兹,大可为僧伽增色也。”南北朝时,佛教来华未久,佛道相争甚为激烈。无论出于寻求自己的依靠,还是出于攻击对方的背景,汉明感梦,永平求法,都成为第一话题。佛教何时初传,反倒不被重视。
“往事越千年”,如今早已不是佛道相争的年代,佛教也不必再用皇权来为自己增色,重寻一个历史的真实,认真做一次千年的回顾、百年的展望,具有更深刻、更重要的历史意义,万邦瞩目,百宗归心,诚为一大事也!
中国学者的论点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佛教史学之大家,首推汤用彤先生。其著名学术专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至今仍为扛鼎之作。吕徵先生评价此书:“受日本人的影响就少,所用资料比较丰富。”关于佛教初传,汤先生认为:
最初佛教传入中国之记载,其无可疑者,即为大月氏王使伊存授《浮屠经》事。
……《裴注》与《世说注》所引相同,而年代又均较早,则谓伊存使汉,博士弟子景卢受经,或较为确实也。
……诸书于授经地点人名虽不相同,但受者为中国博士弟子,口授者为大月氏人,则按之当时情形,并无不合。……据此,则伊存授经,更为确切有据之事也。
关于永平求法(西元67年)
汉明帝永平年中,遣使往西域求法,是为我国向所公认佛教入中国之始。……然使永平年前未传佛法,则不但哀帝时伊存已授佛经,明帝时楚王英已为桑门伊蒲塞设盛馔,其时已有奉佛者在,且即就此传说本身言之,傅毅已知天竺有佛陀之教,即可证当时朝堂已闻有佛法。……至若佛教之流传,自不始于东汉初叶。
学界、教界的另一位大学者、佛教思想专家吕徵先生则认为:
一般采用的,就是见诸记载而事实上也有可能的,乃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以佛经的材料。认为这就是佛教传入的开始。
就当时所掌握的资料而言,吕先生对大月氏是否信佛尚存疑问:
日人白鸟库吉认为,贵霜王朝前二代是不信佛教的,而大月氏又在贵霜王朝之前,当时是否已有佛教流传,还值得研究,……(见《中国佛学源流略讲》,1961年讲述)
吕徵先生的高足、著名佛学学者杜继文先生曾亲自聆听过吕先生的这段论述。他在1980年参与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一书时,回答了老师的疑问。他认为:
大月氏在公元前二世纪移居大夏后很快就接受当地的风俗文化,因此在公元前一世纪末盛行佛教并由其来华使者口授佛经,是完全可能的。
因此,在接受国家教委委托编写《佛教史》高校教材时,杜继文写道:
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当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事实上,《后汉书·楚王英传》记,永平八年,佛教在皇家贵族层已有相当的知名度,不必由汉明帝始感梦求法。
关于永平求法,吕先生认为:
后人因明帝做过这样一件事(指诏退楚王缣纨),于是就编造出他派人求法取经等一系列故事,内容就复杂起来,说明帝永平七年,由于夜梦金人而派人去西域求法……事实上,这纯属后人的附会。
杜继文则认为:
汉明帝求法说从其基本情节来说是比较可信的,但它只是说明印度佛经进一步向中国传播,而不能说这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见《中国佛教史》)
当代治中国佛教史的,还有郭朋先生。他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一书中说,大体可以认为,佛教的传入,当在两汉之际。……至于佛教传入的具体的确凿年月,则因文献不足,难下定论。
郭朋先生认为“文献不足”,与汤用彤先生所说“确然有据”恰恰相反,不知汤先生引用之文献郭先生如何看。
但郭先生却特意将蒋维乔在1929年编写的《中国佛教史》中的论点视为“一家之言”。
蒋维乔认为:
至明帝时,天竺人来华,朝廷尊重之,……实则中国佛教史,当以安世高、支娄迦谶来时(按:时维桓帝建和初年、公元147年,桓帝末年、公元167年)为始也。
此说其实并非“一家之言”。无独有偶,与蒋先生遥相呼应的,则有黄忏华先生所言:
实际,中国佛教史……始于永平十年后约八九十年,东汉末桓、灵二帝时代。
何以心有灵犀?吕徵先生的介绍或许可做参考:
蒋维乔著的《中国佛教史》,主要取材于(日人)境野(哲)的《支那佛教史讲话》(《支那佛教史纲》)宋前部分;黄忏华著的《中国佛教史》,则大体仿照宇井(伯寿)的著述;都是以日本人的著作为蓝本的。……这也证明早期中国佛学研究跟随日本人的事实。
跟随的时间久了,往往会忘记原本是人云亦云的旧事。蒋、黄二先生的著作近几年又有影印流通,他们跟随日本人所说的话,则又被不知背景的人们重复。而更可感慨的是,被跟随的日本人早已跟随着研究的深入,变化了自己的说法,倒是一些忠厚的中国人却还在沿袭他们的旧说。
不过,蒋维乔在1928年出版的《中国佛教史》中也讲到:“魏书所载,可称实录。……知其所载景宪事亦足据。盖此时佛教当已盛行月氏也。”
而黄忏华先生在50年代撰写《中国佛教》中的《中国佛教史略》“后汉佛教”条目时,则明确写道:
……以上诸说,基本上是以佛教初传于汉代为主;但除伊存授经一说外,大多数由于和道教对抗,互竞教兴的先后,遂乃将佛教东传的年代愈推愈远,所有引据大都是虚构和臆测的。……关于汉明求法事既有以上种种异说,所以现代佛教史家怀疑到汉明是不是有求法一事,摩腾、法兰是不是实有其人?这个问题现在还有争论,未能决定。
如果追述到1922年,梁启超先生在《中国佛教研究史》中则指出:
月氏使臣对于佛教有信仰,而我青年学子之怀抱新思想者,从而问业,亦意中事。
近年来,台港地区的佛教史研究也逐渐深入。关于佛教初传的论述,以台湾佛光出版社1987年所出《佛教史年表》最为明确:
大月氏之使节伊存口授浮屠经予博士弟子景卢为中国佛教之始。
该《年表》编纂数年,鸠集人力,广搜资料,参考了历代佛教之编年史书,以及望月佛教大辞典所附之年表、山崎宏之佛教史年表、中国佛教史辞典、日本佛教史辞典、日本史辞典、世界年表、东方年表、韩国佛教史所附之年表,是一部较为出色的教史工具书,它的观点值得我们给以足够的重视。
日本学者的论点
在众多外国学者中,对中国佛教史有较深入研究的,当首推日本学者。为了便于参照,现将其部分著名学者的论述大体依年代前后摘编如下:
宇井伯寿《支那佛教史纲》(昭和11年1936年):
后汉明帝永平十年(纪元六十七)……为公然的佛教初传,乃是从来的定说似的。可是,后来由于学者的研究,逐渐明了,这个永平十年说,并不是传着事实的。因为一般学者不信任永平十年说的全部内容,乃以《魏略》……而取之为佛教之初传中国。
望月信亨《中国净土教理史》(1942年):中国佛教之初传,约在前汉哀帝时代。……鱼豢之〈魏略〉记载,前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有博士弟子景卢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总而言之,这是说明在公元前二年顷,大月氏王之使者,已将佛经以口授传于中国学者,此即中国佛教最初传来之说。
有关佛教最初传入中国之年代,……皆述说在汉明帝时代,明帝夜梦金人,……依于此说,认定明帝永平十年(67年)为中国佛教初传之年代。然而,……这些被认为全系后人所编造。
野上俊静(大谷大学教授)、小川贯贰(龙谷大学教授)、牧田谛亮(京都大学教授)、野村耀昌(立正大学教授)、佐藤达玄(驹泽大学教授)共著《佛教史概说》(1968年初版1975年第7版)
《魏略》之记载,是被近代史家所注目的资料。
史料的可信性高,是佛教初传中最古老的资料,是大有价值的根据。
佛教的经典,是以文字来保存圣法。这被认为是西元之初的事。佛教传入中国,恰巧就在这一时期。
龙谷大学《中国佛教史》教材:
近来诸多学者颇加重视的是载于三国时代《魏略·西戎传》中的史料。……这段历史,是西汉武帝以来开辟西域交通的结果。到西汉末期哀帝之际,佛教在西域地区甚为普及,商人及僧侣进入汉地是当时很自然的现象。
……西汉末期即西纪元年前后,佛教是一种自然的渗透,即所谓“民间传播”。
镰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1985年):
依上所述,后汉明帝的感梦求法说,……明显地是由于历来诸家所研究者,并非史实所传行的。因此,明帝感梦求法被流行的文献均非史实,明显地是后代所虚构。
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实年代,虽然不甚清楚,想来必是随着西域交通道路的开辟,而渐次传播进来。在记录上最为明显的,当是东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据《释老志》)从大月氏使者伊存授予佛经开始。
有关这件事的文献有:鱼豢的魏略西戎传、世说新语文学篇注、魏书释老志、隋书经籍志、辩正论第五、太平御览四夷部等。此外,与此有关联的记事尚有:史记大宛传正义、通典卷百九十六、广州画跋卷二等。此中最古老、最可信赖的资料,该是鱼豢的魏略西戎传。
结 论
综上所述,可知我国古代的佛史记录,有其复杂而深刻的历史背景,关于佛教初传的历史纪年,不可简单地以约定俗成而确认之。
自本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才开始从事现代佛教史学研究,关于佛教初传的历史纪年,初期基本引述日本人的说法,自己虽有研究,并不深入。
50年代之后,针对古代流传的说法和日本人的观点,中国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伊存授经”的论证最为翔实。这种见解在中国学术界逐渐成为主导,并影响到日本等国。随着僧侣的学院化教育日益完善,学术界的观点已逐渐成为教界、学界的共识,某些习以为常的说法正在被更符合历史真实的新的学术成果所取代。争议虽然还会有,但大格局已基本确定。
基于上述学术观点的更新和历史事实的重辨,目前非常重要的工作是使各界人士了解新观点,接受真史实。纪念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是这项工作的最好形式。
将“伊存授经”确认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表明,中国的佛教界和学术界在尊重知识、尊重历史、尊重宗教三方面都显示了文明与文化的进步。历史的真实比皇权的庇护更有力。从教理上讲,这也是“依法不依人”的一大范例。佛法传入东土并得到弘扬光大,正由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智慧、服膺真理的民族,只要是智慧和真理,无论从何方传来,由何人传来,她都会热情地接受、认真地思索、创造性地给以发展。
纪念中国佛教2000年的特殊意义,在于中国佛教是来自印度又有别于印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在于印度佛教已于西元13世纪湮灭,而中国佛教在中国的沃土之上生存发展了2000年却仍保持着走向未来的新的生命力。
由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宗教学会共同确认1998年为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的纪念年,并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名誉会长赵朴初先生亲自确定纪念活动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中国宗教学会协办,这是中国佛教界和中国学术界共襄盛举的一段佳话。
作为历史性的纪念,这是“千载一时,一时千载”的难逢契机,这将促使佛教界、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更加全面了解中国佛教2000年来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相融合的史实,了解汉传、藏传、南传三大系佛教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以及对亚洲乃至世界的深远影响,了解中国佛教的历史趋向及其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广阔前景。
在受到基督教文明影响的所有国度里,西元2000年都得到高度的重视和普遍的关切。其实,那个2000年是以基督诞生之年为起点的一个时间坐标点,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人类文明进程阶段的时间划分形式。庆祝西元2000年,不能说没有意义,但也不像许多人误以为的那样对所有民族都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与对西元2000年的重视和关注相比,我们对中国佛教2000年的重视和关注无论如何都有理由更高更深。没有国家的繁荣昌盛,佛教则难以弘传广布;而佛教的健康发展,必将有助于社会的安乐祥和,人心的弃恶扬善。经历了2000年的风风雨雨,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及中国民众已融为一体。全世界、全亚洲、全中国,包括台湾、香港、澳门,一切虔诚善良的佛教信众和一切关心中国佛教、热爱中国佛教文化的人们,都正把目光转向北京,看我们如何纪念这古老但正在新生的东方宗教的2000年。
回顾与展望,在中国佛教2000年的盛大纪念中,我们记下这历史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