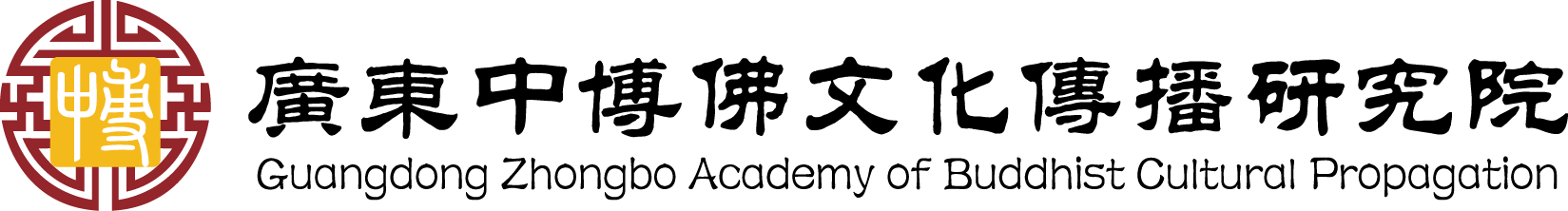峨眉山、成都佛教地处蜀中,两地佛教在历史上有着密切联系。作为名山、城市佛教代表的峨眉山与成都,在佛教发展史上具有典型意义。本文依据史籍、佛经中的有关记载,考察唐宋时期的峨眉山与成都佛教,以展示巴蜀佛教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历史进程。
一、唐宋时期的峨眉山佛教
东晋隆安四年(400),高僧慧持创建峨眉山普贤寺,奠定了峨眉山佛教发展的基础。唐宋时峨眉山普贤道场声名日盛,吸引十方缁素,赴岷峨投诚依栖,建寺造殿。据清蒋超《峨眉山志》记载,唐宋时期峨眉山有光相寺、伏虎寺、华严寺、中峰寺、黑水寺、后牛心寺、万年寺、灵岩寺、棋盘寺、蟠龙寺、香岩寺、观音寺、放光寺、西坡寺等佛寺。峨眉琳宫绀殿,梵呗声声,僧侣云集,习禅修静。峨眉山修行高僧名载山志的,唐代有昌福达道和尚、赵州和尚、黄檗老人、灵龛和尚、白水和尚、洞溪和尚、澄照大师、西禅和尚、慧觉禅师、正性和尚、罗汉和尚、布,水岩和尚、黑水和尚、大乘和尚、东汀和尚、黄龙继达禅师、慧通禅师等。宋代有白水如新禅师、慧直广悟禅师、行明禅师、继业三藏、茂真大师、宗月禅师、密印安尼禅师、慧远禅师、纯白禅师、禅惠大师、别峰禅师、释道宏、峨眉道者等。宋普济《五灯会元》载有峨眉灵岩徽禅师和黑水义钦禅师。这些峨眉高僧,或参禅以冥契佛心,或宏教以启迪众智;或机峰峻发,出语惊人;或精于书画,长于琴棋。他们苦参晦机,严守戒律,开山创院,建立宗纲,使岷峨胜景,渐成丛林。
峨眉山佛教在唐宋时已名显天下,唐宋文士对峨眉佛教之盛多有记载。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八说:
峨眉普贤寺光景殊胜,不下五台。在唐无闻,李太白《峨眉山诗》言仙不言佛,《华严经》以普贤菩萨为主,李长者《合论》言五台山而不言峨眉山。又山中诸佛祠俱无唐刻石文字,疑特盛于本朝也。
邵博言宋代峨眉山佛教兴盛是事实,但说唐代峨眉山无闻却显无据。唐代诗人李白有吟诵峨眉诗三首,其中《峨眉山诗》言仙,而《听蜀僧喉弹琴》、《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人中京》皆言佛。唐代峨眉山与五台山已并峙为南北两大名山,这在佛经中有明确记载。宋赞宁撰《宋高僧传》,说僧人释行明游方礼佛,“初历五台、峨眉,礼金色银色二世界菩萨,皆随心应现”。唐代五台山高僧释澄观,于唐代宗大历十一年(776),“仍往峨眉,求见普贤,登险陟高,备观圣像。……文殊主智,普贤主理,二圣合为毗卢遮那,万行兼通,即大华严之义也”。唐代峨眉山普贤道场,虽僻处西陲巴蜀之地,却名高五岳,四方僧伽信士礼敬普贤者,莫不朝拜峨眉。唐慧立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载:唐高祖武德五年(622),高僧玄奘于人蜀,“住成都空慧寺,……于成都受具,坐夏学律”。玄奘后登临峨眉山,参礼普贤道场,相传九老洞高僧授玄奘佛经一册并佛偈四句曰:
付汝般若舟,慈悲度一切。普贤行愿深,广利无边众。
玄奘得偈豁然开悟,坚定了赴西天求法取经的信念。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二载:
元和十三年(818),倭国僧金刚三昧,蜀僧广升,峨眉人,与邑人约游峨眉。同雇一夫,负笈荷糗药。
此为日本僧人不远万里,慕名参访峨眉的例证。宋代洛阳惠林寺僧圆泽与信士李源,“相约游蜀青城峨眉山”。
峨眉山以佛教名山地位,开始受到唐宋帝王的参礼封敕。唐僖宗于广明二年(881),避黄巢之乱人蜀,僧彻“与杜光庭先生扈从人于峨眉”,⑦作为成都佛道二教的代表,高僧僧彻与高道杜光庭,随同唐僖宗参礼峨眉名山。唐僖宗此行敕建峨眉黑水寺,并赐额永明华藏,又赐住持慧通禅师藕丝无缝袈裟一领及玉环、供器。至宋代太宗、真宗、仁宗三朝赐御制书百余卷,七宝冠、金珠璎珞袈裟、金银瓶钵、奁炉、匙箸、果垒、铜钟、鼓、锣、磐、蜡、茶、塔、芝草等。真宗崇宁中赐钱幡及织成红幡等物。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上记载游历峨眉山,亲见宋仁宗赐白水普贤寺红罗紫绣袈裟,上有御书发愿文曰:
佛法长兴,法轮常转。国泰民安,风雨顺时。干戈永息,人民安乐,子孙昌盛。一切众生同登彼岸。
此发愿文后署书写时间为嘉佑七年(1062)十月十七日。据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记载,宋代常有内侍奉敕往峨眉山烧香祈福。宋欧阳修有《泗州塔下并峨眉山开启袷享礼毕道场斋文》,是峨眉山为国家启建道场的文书。《宋会要辑稿·道释》载大中祥符二年(1009)三月,宋真宗诏:
嘉州白水普贤寺、黑水华藏寺、中峰乾明寺三寺,每年各度行者三人。
宋太祖乾德六年(689),嘉州屡奏普贤显相,太祖遣内使往峨眉庄严瑞象。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遣中使张仁赞赍黄金二千两,于成都铸普贤铜骑象,供奉于白水之源的普贤寺。宋太宗申命中使重修普贤寺,此次大规模重修铸成三千铁佛像,以寓普贤据峨眉有三千徒众共住之意。宋徐铉《大宋重修峨眉山普贤寺碑铭》记重修普贤寺之巍峨壮观曰:
其后则层楼入汉,飞陛连云。彩槛离娄,冠余霞而上出;璇题约砾,缀列宿以旁回。神明之台不足以语其高,天梁之宫不足以矜其丽。铄金为字,写大藏之经秘于上,逾五百函;范铜为像,拟普贤之容设于下,高二十尺。味其文,则如来之宗旨可得而观;礼其相,则菩萨之威神于是乎在。将使三蜀之地,一切有情,皆冲气以含和,尽革凡而成圣。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诏修白水、黑水、华严、中峰、光明等寺,由此峨眉山佛教声誉日隆。
唐宋时期尊崇佛教的社会氛围,峨眉山佛教高僧的学识修持,吸引文人学士上山礼佛参禅,访真探胜。唐代诗人李白、杜甫、岑参、郑谷、贾岛、曹松、薛能、唐球,宋代文人苏轼、范成大、范镇、冯时行、白约都曾登临峨眉,与峨眉高僧唱和酬答,留下饶有兴味的诗文。宋范成大撰《峨眉山行纪》,通过实地考察佛教名山,详细记述了峨眉山佛光、寺庙文物、僧伽传说、名胜古迹,是研究宋代峨眉山佛教的宝贵史料。宋代参礼峨眉山普贤菩萨,已在民间蔚成民情风俗,宋洪迈《夷坚志》补卷第五《双流壮丁》载:
淳熙九年五月未尽之二日,一老媪独行双流县田间。挈青囊,携竹杖,龙钟不克行,困坐道侧。行人问之,答曰:“老婆是关西人,年七十矣!欲往峨眉山礼普贤,不幸抱病。”此关西老人以生命之余年,不惜翻山越岭,千里跋涉,人蜀参礼普贤,可见宋代峨眉山佛教在民间的影响!
二、唐宋时期成都佛教的兴盛
唐宋时期成都梵刹林立,各路高僧云集促成了成都佛教的兴盛。据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载,唐宋成都有大圣慈、圣寿、净众、宝历、昭觉、龙兴、中兴、圣兴、福感、应天、资福、四天王、宁蜀、金华、翠微、草堂等十六寺及福庆禅院。元费著《岁华纪丽谱》记载宋代成都有安福寺、移忠寺、祥符寺、宝历寺、海云寺、信相院、大智院、金绳院等。此外,散见于史籍和佛经中的寺院有:开元寺(孟蜀改延福院)、宝园寺、慈恩寺、菩提寺、宝刹寺、法成寺、法聚寺、福胜寺、福成寺、福化寺、多宝寺、净德寺、宁国寺、国清寺、武担山寺、法云寺、法华寺、龙华寺、妙积寺、鸣鸾寺、延寿寺、回天寺、东禅院、普福禅院、曹溪六祖禅院、洪寿禅师院、天王院、松溪院、大悲院、毗卢院、弘觉禅院等。宋范镇《东斋记事》卷四载:
文潞公任成都府日,米价腾贵,因就诸城门相近寺院,凡十八处,减价粜卖。”此亦从侧面反映成都寺院之多。
唐宋时期的成都佛刹,寺庙佛像法具多有特色。如祥符寺(大中祥符院)的千手眼大悲佛像,高四十七尺,广二十四尺,净众寺的巨钟千钧,都在成都十分著名。安福寺建塔十三级,突兀雄奇,是成都平原登高远眺的去处。宋陆游《雨中登安福寺塔》诗曰:“今朝上黑塔、千里旷无碍。”金绳院以五百罗汉栩栩如生驰名,圣寿寺则是李冰石犀遗迹和蚕丛祠所在。
唐宋时期成都最具影响的佛寺,则是昭觉寺和大圣慈寺。昭觉寺被称为成都福地,始建于唐贞观年间(627—649),最初取名为建元寺,唐宣宗诏休梦禅师应对称旨,敕赐了觉禅师,并赐改寺名为昭觉。宋代人撰的《宝刻类编》卷六,记载成都石刻有:“《昭觉寺记》,萧道撰,中和五年正月,成都。”唐僖宗中和五年(885),萧相国撰写《昭觉寺记》,是记载昭觉寺兴建历史最早的石刻碑文。昭觉寺在宋代历经重建,已是成都颇有规模的佛寺大刹,宋李畋《重修昭觉寺记》说:
兹寺有常住沃土三百廛,涤场敛矫,岁入千耦,井归寺廪,与众共之。有舟航大贾,输流水之钱;山泽豪族,舍金穴之利。五铢一缕,悉归寺府,无一私者。……寺之殿宇,旧且百间,今广而增者三百。……凡供食之丰洁,法席之华焕。时一大会,朝饭千众,累茵敷坐,如升虚邑。
昭觉寺的寺院壁画,显示出名寺的艺术氛围。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卷下记:“唐代名画家张询,中和年随驾到蜀,与昭觉寺休梦长老故交,遂依托焉。忽一日,长老请于本寺大慈堂后留少笔踪,画一堵早景,一堵午景,一堵晚景,盖貌吴中山水,颇甚工。画毕之日,遇僖宗皇帝驾幸兹寺,尽日叹赏。”
如果说昭觉寺初为唐代官员舍宅兴修,而大圣慈寺则是唐玄宗敕建。唐天宝十五年(756),唐玄宗避安史之乱人蜀,敕建大圣慈寺并书额。大圣慈寺共有九十六院,规模宏大,建筑壮丽。唐宋时期益州多名画,而大圣慈寺可谓佛教艺术殿堂。宋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称:
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圣慈寺之盛。……总九十六院,按阁殿塔厅堂房廊,无虑八千五百二十四间。画诸佛如来一千二百一十五,菩萨一万四百八十八,帝释梵王六十八,罗汉祖僧一千七百八十五,天王明王大神将二百六十二,佛经变相一百八十五堵,夹疗雕塑者不与焉。像位繁密,金彩华缛,何庄严显饬之如是。昔之画手,或待诏行在,或禄仕两蜀,皆一时绝艺,格入神妙。至于本朝,类多名笔,度所酬赠,必异他工,资费固不可胜计矣。其铸象以铜,刻经以石,又不可概举。
北宋苏轼《胜相院经藏记》说大圣慈寺“故中和院,赐名胜相,以无量宝,黄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众香,庄严佛语及菩萨语,作大宝藏”。唐高僧知玄“讲谈于大慈寺普贤阁下,黑白众日计万许人,注听倾心,骇叹无己”。贯休《禅月集》卷十九,有《蜀王人大慈寺听讲》的诗文。据宋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载,大圣慈寺诸院为国长讲七十三座,诸院《大藏经》计一十二藏。南宋陆游《观华严阁僧斋》诗自注,说大圣慈寺华严阁,“自四月初至七月末,日饭僧数千人”。陆游《天申节前三日大圣慈寺华严阁燃灯甚盛游人过于元夕》诗,亦言大圣慈寺僧侣众多。在唐宋时期的都市佛寺中,大圣慈寺堪称规模宏大的名寺。
唐宋时期的成都佛寺,是高僧荟萃之地。《宋高僧传》载有无相、法江、道因、神会、僧缄、南印、定兰、定光、会宁、员相等,皆为唐五代成都高僧。成都净众寺高僧无相,本新罗国人,开元十六年(728)至长安,得唐玄宗召见。无相禅师后人蜀,赴资中谒智诜禅师。禅宗五祖弘忍传智诜,智诜传无相,故为七祖。无相为宗密所称禅门七家之第二家。无相在成都“劝檀越造净众、大慈、菩提、宁国等寺,外邑兰若钟塔,不可悉数”。无相弟子神会,利根顿悟,冥契心印,德充慧广,郁为禅宗。神会颇得南康王韦皋敬重,神会死后,韦皋为之立碑,白撰文并书,禅宗荣之。
唐五代成都昭觉寺休梦禅师,“具大戒于律师神佑,悟般若于石霜庆诸,参法要于百丈怀海,契心印于洞山良价”。唐僖宗避乱人蜀之时,在成都召休梦禅师说无上策,赐紫磨衲衣等。前蜀国主王建于休梦申尊叔之礼。尔后宗派传袭,真风炳然,昭觉寺住持延美上人即为休梦第五代弟子。唐五代成都东禅院高僧贯休(832—912),俗姓姜氏,字德隐,署号禅月大师。贯休甚得前蜀国主王建礼遇,赐紫衣师号。贯休长于诗书画撰作,时人称其诗体调不下李白、李贺。“宇内咸知善草书,图画时人比诸怀素”,贯休擅长草书,其书法号称草圣,好事者称为“姜体”。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卷六载于怀玉定水禅院见贯休所作书画:
或古体、或玉筋、或柳叶。又一轴题云:“大蜀国龙楼待诏、明因辩果功德大师、翔鳞殿引驾内供奉、羟律论道门选练教授、三教玄逸大师、守两川僧录大师、食邑三千户、赐紫大沙门贯休字德隐。”今人知禅月之号,则以为僧;闻贯休之名,则以为能画。殊不知当时所作神异如此。非特能画,且于诗文尤高,有《西岳集》三十卷,翰学吴融为之序。
唐相张格、韦庄、王锴、周庠、皆有诗纪其事。
贯休禅师于前蜀永平二年(912)灭度,其弟子昙域戒学精微,篆文雄健,重集许慎《说文》行世,并编辑贯休诗为《禅月集》,收录贯休诗作近700首。
五代成都延福院高僧铁幢长老,重兴寺宇,众号延福为铁幢院。其嗣法弟子有神操,神操授道信,道信传曹溪八代嫡嗣元信禅师。元信禅师为华阳人,得法于郢州芭蕉惠情禅师。惠情嗣南塔,南塔嗣仰山,仰山嗣沩山,沩山嗣百丈,百丈嗣江西,江西嗣南岳,南岳嗣曹溪。曹溪八代传人元信禅师主持延福院后,禅法大兴,朝廷赐名觉城禅院。元信禅师开堂讲经,“师问答随机,叩击无滞,故远近道俗,多所归依,前后王臣,靡不钦重”。
宋代成都清风阁文慧大师,中和胜相院宝月大师、文雅大师、皆为蜀中著名高僧。苏轼《清风阁记》,为应文慧大师之请所作。据苏轼《宝月大师塔铭》所记,宝月大师惟简9岁事中和胜相院慧悟大师为师,后继宗嗣,“其同门友文雅大师惟庆为成都僧,统所治万余人,鞭笞不用,中外肃伏”。宝月大师有弟子士瑜、士隆、绍贤,绍贤为成都副僧统,嗣法徒孙14人,曾孙3人。
宋代蜀中佛教颇盛,宋张方平《蜀州修建天目寺记》说:
百家之聚,必有尸宰堵焉;两楹之室,必有一龛象焉。名都通邑,塔庙固错落相望矣。
宋范镇《东斋记事》卷四载成都僧司大会,观者“填溢坊巷,有践踏至死者,客店求宿,一夜千钱”。元费著《岁华记丽谱》记载宋代成都的民俗活动多在佛寺举行,成都大圣慈寺的药市,圣寿寺的蚕市闻名遐迩。亦见成都佛教与民俗的交融。苏轼《成都大悲阁记》赞叹说:“成都,西南大都会也,佛事最胜!”
三、峨眉山佛教与成都佛教的关系
峨眉山佛教与成都佛教关系密切。早在东晋时期,高僧慧持欲观瞻峨眉,振锡岷岫而人蜀。隆安三年(399),慧持住成都龙渊精舍。经过精心准备,次年登峨眉山辟地建寺,两年后仍回成都龙渊精舍传道修持,直至义熙八年(412)圆寂。南北朝时,印度宝掌和尚云游人蜀,居成都大慈寺,日诵《般若》千言,后携经卷登峨眉礼普贤,建庵修住并注疏佛经,赠送峨眉山僧人。陆游《人蜀记》卷五说:“听诵梵语《般若心经》,此经惟蜀僧能诵。”这与宝掌传教不无关系。
峨眉、成都地处西蜀,从宗教地理的角度看,外方僧人礼峨眉普贤,多要经过成都。随着唐宋峨眉佛教的发展兴盛,人蜀僧人日众,峨眉山佛教与成都佛教的联系更加密切。唐高僧玄奘西游之前人蜀,住成都空慧寺学法,然后登峨眉完成参礼普贤大士之宿愿。昙域《禅月集序》说贯休禅师:“闻岷峨异境,山水幽奇,四海骚然,一方无事。”遂溯江人蜀至成都,前蜀国主王建慕禅师高名,特修禅宇,恳请住持。成都僧人多要赴峨眉朝圣,得以礼拜普贤菩萨,方为真善知识。《宋高僧传》卷二十二《周伪蜀净众寺僧缄传》,即载五代成都净众寺僧缄,“暂去礼峨眉,结夏于黑水方还。”
峨眉山亦有赴成都修习经论、问道讲学者。据清蒋超《峨眉山志》记载,宋峨眉山慧远禅师,出家祝发受具,即往成都习经论,后还峨眉居灵岩寺。峨眉纯白禅师通性相宗经论,遍历成都讲肆讲经。纯白禅师曾住持昭觉寺,元佑末辞昭觉住持之职,又返归峨眉华严寺。宋峨眉密印安民禅师,初讲《楞严》于成都,为义学信众所归服,密印禅师为昭觉寺圆悟禅师嗣法弟子。宋峨眉别峰禅师曾拜昭觉寺圆悟为师,宋陆游《别峰禅师塔铭》说:别峰禅师居峨眉中峰寺,拜密印禅师为师,高僧圆悟南归昭觉,密印遣别峰往昭觉参禅问道,于圆悟门下学习三年,别峰禅师还归峨眉山后,“道望÷日隆,学者争归之,虽圆悟、密印二师,不能掩也”。别峰禅师后再赴成都,“住正法,道既盛行,士大夫亦喜从之游”。
峨眉山僧人与成都僧人,同出于禅宗法嗣。清蒋超《峨眉山志》卷五载:
白水玮禅师,新罗金藏法嗣,曹山本寂孙,与洞山道延弟兄。白水仁禅师,洞山良价法嗣。黑水和尚有二:一黄龙晦机法嗣,岩头全佑曾利、;一沩山灵佑法嗣,与仰山兄弟,唐昭宗时人,禅灯世谱,偶逸其名。黑水承璟禅师,德山缘密法嗣,云门文偃孙。黑水义钦禅师,承璟法嗣。
成都僧人与峨眉僧人的禅林世系,其法脉同源相承。成都、峨眉僧人皆以《华严经》为宗,宋苏易简撰《施华严经净行品序》,宋人撰《宝刻类编》卷三,载成都有《空慧寺讲华严经碑》,即是《华严经》流行的例证。《宋高僧传》卷三《唐莲华传》载:
南天竺乌荼国王书献脂那天子,书云:“手自书写《华严经》百千偈中所说善财童子五十五圣者,善知识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谨奉进上,愿于龙华会中奉觐云”,即贞元十一年也。至十二年六月,诏于崇福寺翻译,;罽宾沙门般若宣梵文,洛京天宫寺广济译语。西明寺圆照笔受,智柔、智通缀文,成都府正觉寺道恒、鉴虚润文,千福寺大通证义,澄观、灵邃详定,神策军护军中尉霍仙呜、左街功德使窦文场写进,十四年二月解座。
参加此次译《华严经》梵夹本后分四十卷的多为两京高僧,而远请成都高僧道恒、鉴虚润文,说明成都高僧对《华严经》颇有研究。宋普济《五灯会元》卷十九《昭觉克勤禅师》,载圆悟克勤政和年间游荆南,与张无尽“剧谈《华严》旨要,曰;‘《华严》现量境界,理事全真,初无假法。所以即一而万,了万为一。一复一,万复万,浩然莫穷。心佛众生,一二无差别。卷舒自在,无碍圆融,此虽极则,终是无风匝匝之波。’(张)公于是不觉促榻”。当时成都高僧多精于禅理,机锋迅捷,棒喝猛烈。
唐宋时期成都佛寺亦崇祀普贤,各寺庙多供奉普贤大士神像。唐韦皋《再修成都府大圣慈寺金像普贤菩萨记》曰:
大慈寺普贤象,盖大照和尚传教沙门体源之所造也。仪合天表,制侔神工,莲开慈颜,月满毫相。昔普贤以宏誓愿于南赡部州赞释迦文,拔群生苦,而尘俗昏智,莫睹真像。虽同诸法,究竟寂寞,而随所应,为现其身,即色即空,皆菩萨行。
宋黄休复《盖州名画录》说,成都佛寺多绘普贤真容,图华严九会。宋范成大游历峨眉山时,所见牛心寺佛画笔迹超妙,当时成都佛画名家卢楞迦,其源流即峨眉山佛画。
唐宋成都写经印经皆极盛行,成都龙池坊卞家、西川过家印佛经有名,今敦煌文书中即有西川过家本佛经。唐代江陵龙兴寺僧人义孚,府主“俾赍钱帛,诣西川写藏经”。峨眉山所用佛经,则来自成都印经坊,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上载峨眉山白水普贤寺有经藏,“经书则造于成都,用碧睡纸销银书之,卷首悉有销金图画,各图一卷之事。”
结 语
宋代范成大、陆游等文士的宗教文化之旅,是溯长江而上入蜀参礼沿途佛寺,其游历终点就是成都、峨眉山的佛寺,岷峨异境,山水幽奇,使文士们流连忘返,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峨眉山普贤道场与五台山文殊道场并峙,是唐宋时期僧伽信士礼佛朝拜之两大名山。唐宋时期成都梵刹林立,高僧云集,蔚为西南佛国。唐宋时期封建社会发展至高峰,佛教文化亦因此出现空前的繁荣。峨眉山和成都佛教相互依存、交融,共同发展、兴隆,谱写出巴蜀佛教的辉煌历史篇章。可以说峨眉山与成都佛教的发展、交流、积淀,构成巴蜀佛教的两大热点区域,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巴蜀佛教文化。